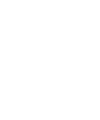壹鬓头春(十四) ⓎúzⒽǎιшú.ρш
帐内流动着温暖的气息,梅沉酒睁开眼张了张唇,发现喉咙干得发紧。矮炉下的木炭已经被熄灭多时,只有烛台上的火苗还在跃动。
周遭的风雪声相较昨夜已经减小许多,但还是能让听者感受到寒意。她从榻上起身,紧接着去重新热茶。
远隔千里仍旧难以安眠,这是她不曾料想到的。梅沉酒伸手探了探背后的冷汗兀自叹息,本以为离开建康能得些喘息的间隙,却被赵海和商崇岁两人的话拽回现实——她累债而活,挣扎不得。
梅沉酒没有逃避的念头,却也头一次感受到了旧事积压的不安。如同昨夜那场毫无征兆的大雪,虽然掩去了原本的黄土,但总有一天事实会重新浮上岸来。而她,既要在覆雪之上有所作为,又要时刻惦念自己的底色。
茶盖被涌出的蒸汽顶得摇晃,梅沉酒无意识伸出僵冷的手去提茶,却被烫得缩回了手。指侧瞬间漫上红,她却连私心的怨怼也没有。
赵海的说辞并无特别之处,反倒是不曾与她打过哑谜的商崇岁让她留了心眼。冒风雪而至,抛下一个毫无来由的疑问后又匆忙离去。若不是有身在商府的这些年可依,她也许要猜测商崇岁与赵海两人是商量着来揭她伤疤的。йρгΘùщēй.Θгɡ(nprouwen.org)
梅沉酒垂下眼,漆黑的瞳孔里连炉火也显得黯淡。商崇岁既说“人皆有因无果”,而拿弘德对沙弥授道时提及的“因果轮回”作答又不让他满意。
有因无果。梅沉酒在心底嚼烂般反复默念这四个字,良久只发出一声冷哼。
不打算再多做纠缠。按捺下那些不愉快后,弘德曾经的告诫又重新归于她的耳际。时隔多年,梅沉酒早已无法将他当初絮叨的字字句句牢记,却能想象得出人一副笑意温柔,无奈摇头的模样。
梅沉酒自觉弘德果真是出家人,她当初仅是仗着孩童身份来插科打诨,他也任由自己胡闹,心软得不像话。越是这样细想,梅沉酒就愈发想要回忆起弘德的样貌。冷不防地,印象里落下的竟成了祁扇那张含笑的脸。
祁扇当初在白鹭洲同她提及,说她抚琴的习惯尤像他的一位故人,骇得她脊背发凉。现在想来,简直可笑至极。弘德容貌清俊气质沉静,而祁扇虽端君子貌以笑示人,但眉眼多算计,教人不敢接近。这样的两人,又有何相似可言。
思及此处,热好的茶刚过梅沉酒的喉。她放下茶碗,蓦地失了兴致。茶水寡淡,又何需再品。想罢便正襟振袍,掀帘而出。
四围的天色还未完全亮起,石青与乌墨交织成一番绮丽。风雪未曾停歇,簌簌落在梅沉酒的头顶和两肩。黄土上厚实的浑白让人看了直想讨趣,她抬脚又放下,“嘎吱”的声音就在一片静谧中传开。
雪天发冻是很正常的,好在营里的风很小。梅沉酒搓着双手,两脚难得俏皮地踮起试图眺望远方。可惜不论是什么景色都被蒙上了一层雾气,唯有黢黑的山影入她双目。
梅沉酒深吸一口气,本打算再在周围随意走走,耳边突然传入的细碎声响让她一愣。时辰尚早,连守夜的士卒也撤去大半,又会有谁闹出这样的声响。梅沉酒屏气凝神,寻声走了十步有余,才发现几帐之后有两人相对而谈。定睛一看,原是宁泽和潘茂豫。
依梅沉酒的考量,她本不该正面出现在两人跟前。可想到宁泽和她提起与潘茂豫相处时的不快,思索片刻后还是决定上前一步,与平常无异地向两人行礼,“潘大人,宁将军。”
宁泽显然有些意外,转身朝她一抱手,“梅公子。”衣甲上落下纷纷白雪,被人随意拍去。
潘茂豫见到踱步而来的梅沉酒,眼里带了些意味深长,“梅公子如何这么早就起了。”
话一出口,早已没了昨日那般顽闹的态度。梅沉酒警觉道,“不瞒潘大人,昨夜风雪声大如嚎啕,在下实难安眠。本就惦念着为君分忧,便在榻前坐了一整夜。”
潘茂豫的脸色稍有好转,点头道,“你倒是有心。”
他这话虽轻,梅沉酒却不敢再回应。若不是她擅自前来搅了两人的谈论,或许现今也不会叁顾无言。如此不凑巧,还是先前在西园那回撞见左先光处置杨平。
宁泽很知分寸地噤声,却面色冷然。潘茂豫的视线则在梅沉酒身上来回扫动,出其不意地将话题一抛,“梅公子和祁扇祁大人可相识?”
语气里又端十分客气。梅沉酒张口便答,“见过一面。不过是回走诗游船的交情,算不得熟络。”她强忍下拧眉的冲动,心底的焦虑聚成一团。
潘茂豫闻言脸色骤然阴沉,须臾眉心又笑着松释开。梅沉酒甚至还没来得及看清他脸上的情绪变化,人就已经来到她跟前,亲为掸雪,“要说这建康城内的才俊,就属你不一般。不然怎么会被那位打上主意?”
梅沉酒瞳孔一缩,赶忙俯身做礼,“在下惶恐”
“梅公子先前遇见的祁扇正是此次梁国派来的外使,他在一个时辰前遣人递了封信来,邀你去依木山观景。”潘茂豫对她这番如临大敌的态度置若罔闻,语气里辨不出喜怒。
“依木山?”梅沉酒抬头望向潘茂豫。且不说这天气是否合适赏景,单是祁扇北梁外使的身份便不能轻信。虽不至于大动干戈,但万一是场争利的鸿门宴,南邑在邢州之事上就落了下乘。
宁泽适时走上前来,向她颔首肯定道,“正是依木山。此山横亘梁邑,也是两国历代协定的边界。”
“那两位大人的意思是?”话里虽含犹疑,梅沉酒心底已有了几分计较。
潘茂豫面上带笑,言语间透出威压,“咱家方才正与宁将军商讨,凑巧你就来了。此事与你有关,我们便不好相瞒。”
真正与潘茂豫此人就事论事说上几句,才能明白宁泽话里透露的“难缠”是何意。梅沉酒摇头似叹,“让潘大人忧心了,在下行事毫无怨言。只是我若要应下此约,虽是孑身前去,也恐有诈危及旁人。不知潘大人意下是?”
“宁将军自会陪同。”潘茂豫收回手,从袖中取出封黄纸信交给梅沉酒。她老实接过,恍然宁泽的脸色如此难看,原是被潘茂豫逼迫却又无可奈何。
“梅公子应该不需要再做其他准备了吧?”宁泽的插话让梅沉酒一惊,她从信纸上抬起头来定定地看向人,听得他紧接的话。
“既然如此,那就尽早出发。白日里我有军务在身,不能离开营地太久,还望公子谅解。”字句掷地有声,让人没有反驳的余地。要不是梅沉酒与他熟识,她还真的以为是自己不受这个小将军待见。
梅沉酒讪笑道,“听凭宁将军吩咐。”
宁泽得到答复后也不客气,转身便走。梅沉酒顿时瞪大了两眼,看着他的背影似噎住了气,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反倒是置身事外的潘茂豫出言叫人跟上,梅沉酒才匆匆作别。
纷扬飘雪间,两人不断踩下湿滑的脚印。冷冽寒风擦过梅沉酒的耳际呼啸向后,偶有雪片贴在她的脸颊融化,留下的水渍像是就着湖面捅穿的冰窟窿。
身侧的营帐逐渐变少,宁泽叮嘱梅沉酒站在原地不动,自己前去马厩牵了两匹马来。牵绳递予她时,平静道,“出了关城地界风就会转小,还望公子跟紧我。”
梅沉酒点点头翻身上马,扑面而来的雪雾模糊了她的视野。身旁的宁泽则勾拽缰绳,两腿夹马肚走得悠闲。她叹了口气,一路上两眼得闲,脑中便自然浮现出信上俊逸的字迹。
“彼时白洲逢汝,虽寥寥几语相谈,却得他乡之可爱。只恨草草相别,难表欣然。遂今时今日既身有相异,也望汝尚安异事,且谈依木怡景。入夜起信,但凭”
思绪戛然而止,梅沉酒呼出一口白气,懊恼自己没有多看几遍。
“你是在想那封信,还是在想接下来的打算?”宁泽突然回头看了一眼,拉马凑近梅沉酒。
“信。”梅沉酒伸手拭脸,打算重从袖里取那黄纸,“总觉得信里有些蹊跷。”
“入夜起信,但凭薄纸托意,不至不归。”宁泽立刻背出信文,附和道,“你也觉得这句话奇怪?”
“你是把这信吃进肚了不成?他写的什么你都能记得一清二楚。”梅沉酒缩回伸到一半的手,向人分析,“信中墨痕发陈,定然不是今夜书写;说是邀会,却又不约时辰像是掐准了我的行迹。”
宁泽气急败坏,“我还真就是把这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。要不是潘茂豫闲得睡不着觉在外面瞎晃悠,我说不定早就把信烧了,哪还轮得到你这样推断。”
“祁扇好歹也是北梁外使,你若轻易烧了他的信,到时候人入南邑,说不定就要变着法儿地来磋磨你。”梅沉酒一顿后道,“我觉得奇怪的不止那信,还有潘茂豫。他既受皇命来关城行监察之职,就当将祁扇来信一事告知其他官员。如何能笃定祁扇只为邀我赏景,而非有其他打算?”加之那催促的态度,像是巴不得让她赶紧去了了事的。
宁泽轻啧一声,面色古怪,“他这不眠不休,难不成就等着截我的信?”
“宁将军英武豪迈,建康城内多少姑娘望眼欲穿,结果竟让一个寺人捷足登先这翘首盼归的机会?”梅沉酒忍俊不禁,复又道,“此事暂且不谈,看你一路也忍得辛苦,想说什么便说罢,我都听着。”她怎么会没看出他几次叁番地欲言又止。
“既然看出来了,就早该让我说你也知道我藏不住话。”宁泽失笑,他抿了抿唇,语气认真,“梅沉酒,我知道这世上早就没有能够让你完全信任的人。但他们,却只能信我。”
宁泽了解她的防备,甚至赞同这样的多疑,所以他会像寻常献忠的臣子一样思考如何让君者打消担忧。以至于守夜的部下明明该在晨间把信上呈,却偶然撞见了孤身站在风雪中的将军,也让宁泽不得不与潘茂豫来上一场堪称激烈的争执。
梅沉酒几乎在瞬间就反应过来宁泽口中的“他们”指的是谁,她侧过脸与人对视,给予肯定,“那便等你觉得时机到了,再和我仔细说说玄羽骑的事罢。”
风果然如宁泽所言在两人说话时逐渐转小,原本迷蒙的山影也变得清晰起来。苍穹与雪白的峰顶相接,云霭显现其间。
“方才忘了跟你说,此山并非依木山全貌,而是依木山的支脉。”宁泽思索片刻,忽得皱起了眉,“祁扇说邀你赏景,大概会上山。但我现今身份敏感,不能轻易陪你上去。”
梅沉酒点点头,“我并不担心有什么危险,只是想到要应付祁扇觉得有些费神罢了。”
“早些年我巡山时上去过一次,风景倒也不错。虽然关城遍地黄沙没什么好看,但毕竟登高望远,心境难免会有不同。”宁泽宽慰道,“要是他说不出什么好话,你就权当自己在看景。”
马踏飞雪疾行,笑闹之间已至山前。梅沉酒远远望见连绵起伏的山脉,心情不由得舒畅起来。而山下仅伫立一人,他白袍翩翩,似要与霜天雪色融为一体,就那疏朗之姿。
梅沉酒心念一动,不再说话。她的确未曾料到祁扇邀她赏景,便真就直截了当地孤身前来,不复先前那般多使心眼。
宁泽拽紧缰绳歇马时,前蹄扬起不小的雪屑,祁扇稍稍往旁退了几步,眼里未露不满。
“祁大”梅沉酒下马向人行礼,那声称谓还未出口就被祁扇抬手制止。
“不过是个私下的邀约,梅公子要是拿那些虚名来应付我,可就太不客气了。”祁扇语气恳切,似是真为她的应邀而高兴,接着目光转向宁泽,脸上笑意不变,“这位是?”
宁泽面色肃然,对祁扇的客套视若无睹。他将另一匹马的牵绳套到手中后才淡淡道,“宁泽。”言简意赅,毫无表明身份的意愿。
祁扇得了答复便不再多问,察觉到宁泽显然的敌意后更是坦然迎上那审视的眼神。
站在中间的梅沉酒嘴角抽搐,对这莫名的较劲头疼不已。宁泽算半个倔脾气,祁扇也不是善茬,偏生这两个人碰到一块儿。半晌,她翕张着唇,终是开了口,“在下”
“在下今日能邀到梅公子赏景,还要多谢宁大人相送。如今风雪转小,我也不好耽搁,只是辛苦宁大人在山下留候了。”话毕,祁扇就朝梅沉酒一笑,径自擦身离去。
梅沉酒微不可察地松了口气,与宁泽对视一眼后提步跟上。
“梅公子可知这山的名字?”冻得惨青的石阶上落下一双乌皮靴,轻柔的声音似乎要随风逸散。白衣纤尘不染,唯有下摆一围的回字暗纹被雪水濡湿,隐隐透出银灰的色泽。
梅沉酒攥紧下裙的手一松,站直身后从半山腰往下望去。果真如宁泽所言黄沙莽莽,就连成片的关城也微若星点。她开了口,无端有股落寞,“我从未来过邢州,自然也不知这山的名字。”
祁扇听见身后渐渐没了声响,仅余寒风穿袖而过。他脚步一顿,转过身正对梅沉酒,“既然如此,我便自作主张替梅公子说一说这依木山了?”似是怕人在山间听不真切,他微倾身,将她完全拢在自己的阴影之下。
梅沉酒刚想拾级而上,抬头便于祁扇四目相对。他将她眼前还未透亮的天色遮得一干二净,梅沉酒不知祁扇是有心还是无意。她略一点头,笑道,“那就有劳了。”
祁扇见梅沉酒答复后收回视线继续看景,眼中若有所思。紧接着他转过身,继续前行,“此山在北梁典籍中少有记载,我四处查阅,才在一部东凉物志图谱上找见。原来‘依木山’非‘依木’,是为‘遗母’。”
“早听闻东凉人好崇拜。把山视作遗落的亲族,也算情有可原。”见着祁扇稳当地踩着台阶向上,梅沉酒深吸了一口寒气抬头望向将晓的天际,嘴角慢慢浮起冷笑。她并非是个叁岁稚儿来听祁扇讲这些奇闻轶事的,邢州一事错综复杂,他竟有心思来与她谈天说地。
“梅公子说的不错。此山虽为支脉,却是东凉的母山。”祁扇思索片刻后接着道,“正元百年间,依木山的确也曾归属东凉。”
“正元”梅沉酒弯腰提裙,右脚向上迈了一步。她正想顺着祁扇的话应下,却在张嘴那一刹那生硬地改了口,“恕在下见识疏浅,正元莫不是北梁的年号?我生在南邑,未曾听闻‘正元’一说。”
若她没有记错,“正元”二字仅用以记述北梁统历,而晏佑对南邑坊间流通的书籍严加管控,像商家嫡子这样身份的普通人应当难以得知此事。
梅沉酒闭了闭眼,旧时宫中所藏的北梁籍册不在少数,后入商府又知商崇岁原是北梁出身,“正元”一说如影随形,才会让她下意识放松了警惕。
半人高的树丛摇晃着枯瘦的枝干,不堪重负般卸下头顶厚重的白雪,将它们扑进山石的缝隙间。梅沉酒小心翼翼踩着石阶,还陷在自己的考量中,甚至不曾发觉漫天飞雪已经止息。直到前头的白衣忽得没了踪影,她才堪堪抬起头。
尽管因为高处的霜冻而难以长出繁茂的绿叶,无名之树仍于崖壁间傲然挺立。欺霜的姿态丝毫不容小觑。
梅沉酒收回视线,发现行路受阻。不知从山间何处滚落的巨石突兀地显在路中央,将她的两眼塞得满满当当。如果她不留神地再进上方寸,保不准就会在额上留下疤痕。
梅沉酒对这横祸似的意外一时无言。但在毫无庇护且陡峭的山壁间她也不敢轻举妄动,只好侧过身,扶着石块弯腰查看情况。
巨石将那仅有叁步宽的狭窄台阶砸了个粉碎,本就是艰难容人的距离,现下却是怎么都无法跨过了。
梅沉酒正抱臂发难,一只手便越过石块伸至她眼前。骨节修长若竹,指侧的薄茧清晰可见,唯有掌心落下些焦黑的木屑。
“来。”
--
周遭的风雪声相较昨夜已经减小许多,但还是能让听者感受到寒意。她从榻上起身,紧接着去重新热茶。
远隔千里仍旧难以安眠,这是她不曾料想到的。梅沉酒伸手探了探背后的冷汗兀自叹息,本以为离开建康能得些喘息的间隙,却被赵海和商崇岁两人的话拽回现实——她累债而活,挣扎不得。
梅沉酒没有逃避的念头,却也头一次感受到了旧事积压的不安。如同昨夜那场毫无征兆的大雪,虽然掩去了原本的黄土,但总有一天事实会重新浮上岸来。而她,既要在覆雪之上有所作为,又要时刻惦念自己的底色。
茶盖被涌出的蒸汽顶得摇晃,梅沉酒无意识伸出僵冷的手去提茶,却被烫得缩回了手。指侧瞬间漫上红,她却连私心的怨怼也没有。
赵海的说辞并无特别之处,反倒是不曾与她打过哑谜的商崇岁让她留了心眼。冒风雪而至,抛下一个毫无来由的疑问后又匆忙离去。若不是有身在商府的这些年可依,她也许要猜测商崇岁与赵海两人是商量着来揭她伤疤的。йρгΘùщēй.Θгɡ(nprouwen.org)
梅沉酒垂下眼,漆黑的瞳孔里连炉火也显得黯淡。商崇岁既说“人皆有因无果”,而拿弘德对沙弥授道时提及的“因果轮回”作答又不让他满意。
有因无果。梅沉酒在心底嚼烂般反复默念这四个字,良久只发出一声冷哼。
不打算再多做纠缠。按捺下那些不愉快后,弘德曾经的告诫又重新归于她的耳际。时隔多年,梅沉酒早已无法将他当初絮叨的字字句句牢记,却能想象得出人一副笑意温柔,无奈摇头的模样。
梅沉酒自觉弘德果真是出家人,她当初仅是仗着孩童身份来插科打诨,他也任由自己胡闹,心软得不像话。越是这样细想,梅沉酒就愈发想要回忆起弘德的样貌。冷不防地,印象里落下的竟成了祁扇那张含笑的脸。
祁扇当初在白鹭洲同她提及,说她抚琴的习惯尤像他的一位故人,骇得她脊背发凉。现在想来,简直可笑至极。弘德容貌清俊气质沉静,而祁扇虽端君子貌以笑示人,但眉眼多算计,教人不敢接近。这样的两人,又有何相似可言。
思及此处,热好的茶刚过梅沉酒的喉。她放下茶碗,蓦地失了兴致。茶水寡淡,又何需再品。想罢便正襟振袍,掀帘而出。
四围的天色还未完全亮起,石青与乌墨交织成一番绮丽。风雪未曾停歇,簌簌落在梅沉酒的头顶和两肩。黄土上厚实的浑白让人看了直想讨趣,她抬脚又放下,“嘎吱”的声音就在一片静谧中传开。
雪天发冻是很正常的,好在营里的风很小。梅沉酒搓着双手,两脚难得俏皮地踮起试图眺望远方。可惜不论是什么景色都被蒙上了一层雾气,唯有黢黑的山影入她双目。
梅沉酒深吸一口气,本打算再在周围随意走走,耳边突然传入的细碎声响让她一愣。时辰尚早,连守夜的士卒也撤去大半,又会有谁闹出这样的声响。梅沉酒屏气凝神,寻声走了十步有余,才发现几帐之后有两人相对而谈。定睛一看,原是宁泽和潘茂豫。
依梅沉酒的考量,她本不该正面出现在两人跟前。可想到宁泽和她提起与潘茂豫相处时的不快,思索片刻后还是决定上前一步,与平常无异地向两人行礼,“潘大人,宁将军。”
宁泽显然有些意外,转身朝她一抱手,“梅公子。”衣甲上落下纷纷白雪,被人随意拍去。
潘茂豫见到踱步而来的梅沉酒,眼里带了些意味深长,“梅公子如何这么早就起了。”
话一出口,早已没了昨日那般顽闹的态度。梅沉酒警觉道,“不瞒潘大人,昨夜风雪声大如嚎啕,在下实难安眠。本就惦念着为君分忧,便在榻前坐了一整夜。”
潘茂豫的脸色稍有好转,点头道,“你倒是有心。”
他这话虽轻,梅沉酒却不敢再回应。若不是她擅自前来搅了两人的谈论,或许现今也不会叁顾无言。如此不凑巧,还是先前在西园那回撞见左先光处置杨平。
宁泽很知分寸地噤声,却面色冷然。潘茂豫的视线则在梅沉酒身上来回扫动,出其不意地将话题一抛,“梅公子和祁扇祁大人可相识?”
语气里又端十分客气。梅沉酒张口便答,“见过一面。不过是回走诗游船的交情,算不得熟络。”她强忍下拧眉的冲动,心底的焦虑聚成一团。
潘茂豫闻言脸色骤然阴沉,须臾眉心又笑着松释开。梅沉酒甚至还没来得及看清他脸上的情绪变化,人就已经来到她跟前,亲为掸雪,“要说这建康城内的才俊,就属你不一般。不然怎么会被那位打上主意?”
梅沉酒瞳孔一缩,赶忙俯身做礼,“在下惶恐”
“梅公子先前遇见的祁扇正是此次梁国派来的外使,他在一个时辰前遣人递了封信来,邀你去依木山观景。”潘茂豫对她这番如临大敌的态度置若罔闻,语气里辨不出喜怒。
“依木山?”梅沉酒抬头望向潘茂豫。且不说这天气是否合适赏景,单是祁扇北梁外使的身份便不能轻信。虽不至于大动干戈,但万一是场争利的鸿门宴,南邑在邢州之事上就落了下乘。
宁泽适时走上前来,向她颔首肯定道,“正是依木山。此山横亘梁邑,也是两国历代协定的边界。”
“那两位大人的意思是?”话里虽含犹疑,梅沉酒心底已有了几分计较。
潘茂豫面上带笑,言语间透出威压,“咱家方才正与宁将军商讨,凑巧你就来了。此事与你有关,我们便不好相瞒。”
真正与潘茂豫此人就事论事说上几句,才能明白宁泽话里透露的“难缠”是何意。梅沉酒摇头似叹,“让潘大人忧心了,在下行事毫无怨言。只是我若要应下此约,虽是孑身前去,也恐有诈危及旁人。不知潘大人意下是?”
“宁将军自会陪同。”潘茂豫收回手,从袖中取出封黄纸信交给梅沉酒。她老实接过,恍然宁泽的脸色如此难看,原是被潘茂豫逼迫却又无可奈何。
“梅公子应该不需要再做其他准备了吧?”宁泽的插话让梅沉酒一惊,她从信纸上抬起头来定定地看向人,听得他紧接的话。
“既然如此,那就尽早出发。白日里我有军务在身,不能离开营地太久,还望公子谅解。”字句掷地有声,让人没有反驳的余地。要不是梅沉酒与他熟识,她还真的以为是自己不受这个小将军待见。
梅沉酒讪笑道,“听凭宁将军吩咐。”
宁泽得到答复后也不客气,转身便走。梅沉酒顿时瞪大了两眼,看着他的背影似噎住了气,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反倒是置身事外的潘茂豫出言叫人跟上,梅沉酒才匆匆作别。
纷扬飘雪间,两人不断踩下湿滑的脚印。冷冽寒风擦过梅沉酒的耳际呼啸向后,偶有雪片贴在她的脸颊融化,留下的水渍像是就着湖面捅穿的冰窟窿。
身侧的营帐逐渐变少,宁泽叮嘱梅沉酒站在原地不动,自己前去马厩牵了两匹马来。牵绳递予她时,平静道,“出了关城地界风就会转小,还望公子跟紧我。”
梅沉酒点点头翻身上马,扑面而来的雪雾模糊了她的视野。身旁的宁泽则勾拽缰绳,两腿夹马肚走得悠闲。她叹了口气,一路上两眼得闲,脑中便自然浮现出信上俊逸的字迹。
“彼时白洲逢汝,虽寥寥几语相谈,却得他乡之可爱。只恨草草相别,难表欣然。遂今时今日既身有相异,也望汝尚安异事,且谈依木怡景。入夜起信,但凭”
思绪戛然而止,梅沉酒呼出一口白气,懊恼自己没有多看几遍。
“你是在想那封信,还是在想接下来的打算?”宁泽突然回头看了一眼,拉马凑近梅沉酒。
“信。”梅沉酒伸手拭脸,打算重从袖里取那黄纸,“总觉得信里有些蹊跷。”
“入夜起信,但凭薄纸托意,不至不归。”宁泽立刻背出信文,附和道,“你也觉得这句话奇怪?”
“你是把这信吃进肚了不成?他写的什么你都能记得一清二楚。”梅沉酒缩回伸到一半的手,向人分析,“信中墨痕发陈,定然不是今夜书写;说是邀会,却又不约时辰像是掐准了我的行迹。”
宁泽气急败坏,“我还真就是把这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。要不是潘茂豫闲得睡不着觉在外面瞎晃悠,我说不定早就把信烧了,哪还轮得到你这样推断。”
“祁扇好歹也是北梁外使,你若轻易烧了他的信,到时候人入南邑,说不定就要变着法儿地来磋磨你。”梅沉酒一顿后道,“我觉得奇怪的不止那信,还有潘茂豫。他既受皇命来关城行监察之职,就当将祁扇来信一事告知其他官员。如何能笃定祁扇只为邀我赏景,而非有其他打算?”加之那催促的态度,像是巴不得让她赶紧去了了事的。
宁泽轻啧一声,面色古怪,“他这不眠不休,难不成就等着截我的信?”
“宁将军英武豪迈,建康城内多少姑娘望眼欲穿,结果竟让一个寺人捷足登先这翘首盼归的机会?”梅沉酒忍俊不禁,复又道,“此事暂且不谈,看你一路也忍得辛苦,想说什么便说罢,我都听着。”她怎么会没看出他几次叁番地欲言又止。
“既然看出来了,就早该让我说你也知道我藏不住话。”宁泽失笑,他抿了抿唇,语气认真,“梅沉酒,我知道这世上早就没有能够让你完全信任的人。但他们,却只能信我。”
宁泽了解她的防备,甚至赞同这样的多疑,所以他会像寻常献忠的臣子一样思考如何让君者打消担忧。以至于守夜的部下明明该在晨间把信上呈,却偶然撞见了孤身站在风雪中的将军,也让宁泽不得不与潘茂豫来上一场堪称激烈的争执。
梅沉酒几乎在瞬间就反应过来宁泽口中的“他们”指的是谁,她侧过脸与人对视,给予肯定,“那便等你觉得时机到了,再和我仔细说说玄羽骑的事罢。”
风果然如宁泽所言在两人说话时逐渐转小,原本迷蒙的山影也变得清晰起来。苍穹与雪白的峰顶相接,云霭显现其间。
“方才忘了跟你说,此山并非依木山全貌,而是依木山的支脉。”宁泽思索片刻,忽得皱起了眉,“祁扇说邀你赏景,大概会上山。但我现今身份敏感,不能轻易陪你上去。”
梅沉酒点点头,“我并不担心有什么危险,只是想到要应付祁扇觉得有些费神罢了。”
“早些年我巡山时上去过一次,风景倒也不错。虽然关城遍地黄沙没什么好看,但毕竟登高望远,心境难免会有不同。”宁泽宽慰道,“要是他说不出什么好话,你就权当自己在看景。”
马踏飞雪疾行,笑闹之间已至山前。梅沉酒远远望见连绵起伏的山脉,心情不由得舒畅起来。而山下仅伫立一人,他白袍翩翩,似要与霜天雪色融为一体,就那疏朗之姿。
梅沉酒心念一动,不再说话。她的确未曾料到祁扇邀她赏景,便真就直截了当地孤身前来,不复先前那般多使心眼。
宁泽拽紧缰绳歇马时,前蹄扬起不小的雪屑,祁扇稍稍往旁退了几步,眼里未露不满。
“祁大”梅沉酒下马向人行礼,那声称谓还未出口就被祁扇抬手制止。
“不过是个私下的邀约,梅公子要是拿那些虚名来应付我,可就太不客气了。”祁扇语气恳切,似是真为她的应邀而高兴,接着目光转向宁泽,脸上笑意不变,“这位是?”
宁泽面色肃然,对祁扇的客套视若无睹。他将另一匹马的牵绳套到手中后才淡淡道,“宁泽。”言简意赅,毫无表明身份的意愿。
祁扇得了答复便不再多问,察觉到宁泽显然的敌意后更是坦然迎上那审视的眼神。
站在中间的梅沉酒嘴角抽搐,对这莫名的较劲头疼不已。宁泽算半个倔脾气,祁扇也不是善茬,偏生这两个人碰到一块儿。半晌,她翕张着唇,终是开了口,“在下”
“在下今日能邀到梅公子赏景,还要多谢宁大人相送。如今风雪转小,我也不好耽搁,只是辛苦宁大人在山下留候了。”话毕,祁扇就朝梅沉酒一笑,径自擦身离去。
梅沉酒微不可察地松了口气,与宁泽对视一眼后提步跟上。
“梅公子可知这山的名字?”冻得惨青的石阶上落下一双乌皮靴,轻柔的声音似乎要随风逸散。白衣纤尘不染,唯有下摆一围的回字暗纹被雪水濡湿,隐隐透出银灰的色泽。
梅沉酒攥紧下裙的手一松,站直身后从半山腰往下望去。果真如宁泽所言黄沙莽莽,就连成片的关城也微若星点。她开了口,无端有股落寞,“我从未来过邢州,自然也不知这山的名字。”
祁扇听见身后渐渐没了声响,仅余寒风穿袖而过。他脚步一顿,转过身正对梅沉酒,“既然如此,我便自作主张替梅公子说一说这依木山了?”似是怕人在山间听不真切,他微倾身,将她完全拢在自己的阴影之下。
梅沉酒刚想拾级而上,抬头便于祁扇四目相对。他将她眼前还未透亮的天色遮得一干二净,梅沉酒不知祁扇是有心还是无意。她略一点头,笑道,“那就有劳了。”
祁扇见梅沉酒答复后收回视线继续看景,眼中若有所思。紧接着他转过身,继续前行,“此山在北梁典籍中少有记载,我四处查阅,才在一部东凉物志图谱上找见。原来‘依木山’非‘依木’,是为‘遗母’。”
“早听闻东凉人好崇拜。把山视作遗落的亲族,也算情有可原。”见着祁扇稳当地踩着台阶向上,梅沉酒深吸了一口寒气抬头望向将晓的天际,嘴角慢慢浮起冷笑。她并非是个叁岁稚儿来听祁扇讲这些奇闻轶事的,邢州一事错综复杂,他竟有心思来与她谈天说地。
“梅公子说的不错。此山虽为支脉,却是东凉的母山。”祁扇思索片刻后接着道,“正元百年间,依木山的确也曾归属东凉。”
“正元”梅沉酒弯腰提裙,右脚向上迈了一步。她正想顺着祁扇的话应下,却在张嘴那一刹那生硬地改了口,“恕在下见识疏浅,正元莫不是北梁的年号?我生在南邑,未曾听闻‘正元’一说。”
若她没有记错,“正元”二字仅用以记述北梁统历,而晏佑对南邑坊间流通的书籍严加管控,像商家嫡子这样身份的普通人应当难以得知此事。
梅沉酒闭了闭眼,旧时宫中所藏的北梁籍册不在少数,后入商府又知商崇岁原是北梁出身,“正元”一说如影随形,才会让她下意识放松了警惕。
半人高的树丛摇晃着枯瘦的枝干,不堪重负般卸下头顶厚重的白雪,将它们扑进山石的缝隙间。梅沉酒小心翼翼踩着石阶,还陷在自己的考量中,甚至不曾发觉漫天飞雪已经止息。直到前头的白衣忽得没了踪影,她才堪堪抬起头。
尽管因为高处的霜冻而难以长出繁茂的绿叶,无名之树仍于崖壁间傲然挺立。欺霜的姿态丝毫不容小觑。
梅沉酒收回视线,发现行路受阻。不知从山间何处滚落的巨石突兀地显在路中央,将她的两眼塞得满满当当。如果她不留神地再进上方寸,保不准就会在额上留下疤痕。
梅沉酒对这横祸似的意外一时无言。但在毫无庇护且陡峭的山壁间她也不敢轻举妄动,只好侧过身,扶着石块弯腰查看情况。
巨石将那仅有叁步宽的狭窄台阶砸了个粉碎,本就是艰难容人的距离,现下却是怎么都无法跨过了。
梅沉酒正抱臂发难,一只手便越过石块伸至她眼前。骨节修长若竹,指侧的薄茧清晰可见,唯有掌心落下些焦黑的木屑。
“来。”
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