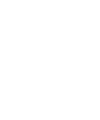(十)静安
这间房,何景梧近两年没进过。
房间面积不大,东西却堆得满满的,一半是各式各样的书籍,一半是情趣玩具。
人总是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,不管用什么方式。
何景梧实在想不起来,自己跟余应晚的关系是何时发生的变化。
如同想不起来读书时的哪一天,黑板上的粉笔字突然长了毛边,再反应过来,已经戴上眼镜。
可是他清楚的记得,余应晚十八岁生日。
那天,何景梧在公司加班,很晚才回家,他以为小姑娘早就睡了,便没开灯。
洗漱完毕,何景梧躺上床,伸手触碰到一具温热的身体。
她躺在他的床上,大腿根部沾着斑驳的血迹,身体不断发抖的,脸色苍白的如纸。
何景梧有那么一瞬间,想打电话叫救护车。
再后来,他看见了床头的玩具。
她说,何景梧,你不要的东西,我也不想要了。
他的小姑娘病了。
他带她去看过很多心理医生,这间屋子里也摆着越来越多的书。
从《学记》到叶圣陶,从蒙台梭利到杜威,从弗洛伊德到荣格。
他们都是古今中外着名的教育学家,心理学家,名字印在一届又一届的教科书上,是权威的代表。
可是他们没有说,该怎么才能治好余应晚。
后来,他也病了。
何家和余家数十年没坐在一起吃饭,再聚一起,气氛是说不出的尴尬。
余应晚对何家那边的人基本没什么印象,只记得何铭威除了何致远外,还有三个孩子,两个在国外,留在洛桑定居的是他最小的女儿何静安。
何静安长得就像她的名字那般,温婉沉静,举手投足间,很是优雅。
众人有意将余应晚推到余霭霞和何致远的中间那个位置,明示暗示几次。
她站在原地,不肯动。
余成安的脸色有些不好,正要说话,只听何静安道:“行了晚晚,你坐在我这边吧。”
何静安坐在最末处,替众人布菜。
象牙筷敲击瓷碗,叮当作响,她的动作小心而又得t,让人舒心,每个人的碗里菜色都不尽相同,就连分量都不一样。
“爸,您有高血压,荤腥要少沾。”最后到了余应晚,何静安放下筷子,轻声询问她的意见,“晚晚,可有什么不爱吃的菜?”
余应晚猛得立起身子摇头,莫名有些拘谨。
何静安笑着说:“不用紧张,都是自家人。”说着,随意替她挑了几样可口蔬菜,还给她夹了一只j腿,“你太瘦,该多吃点。”
整餐饭局,沉闷而又无聊。
余成安会原谅余霭霞,是意料之中的事,毕竟,余家就这么一个孩子。
何铭威原谅余霭霞,余应晚也能理解。
余成安虽然退休,政界的威望还在,趁着最后的余热,何家如果自己又争气,路会越来越好走。
最让余应晚不明白的是,何致远竟然也能原谅余霭霞,如果真正爱过的话。
余霭霞确实是令人难忘的女子。
她生得美而娇艳,尤其是那双凤眼,狭长的眸,眼角处上扬,不笑都狐媚勾人的那种。
她的t态也很好,四肢纤细,柳腰直背,浅蓝色的碎花裙,背后的部分遮一半漏一半,隐约可见白皙水嫩的肌肤。
但跟同样温婉典雅的何静安相b,她又太不象话,吃饭中还不时的同何致远低语,两人看上去感情不错。
话题移到孩子们身上。
余霭霞终于抬头看了余应晚和何景梧一眼,淡淡微笑,算是打过招呼,过后又开始跟何致远低声聊天,仿佛坐在对面的,不是她的儿女,只是两个刚认识的人。
余霭霞可不是故意的,余应晚敢保证,她看过电视上王菲无视记者镜头,坐在谢霆锋身后玩手机的那张照片,也是这般姿态。
有些人即使身处人群,也跟人群隔着一层,不食人间烟火大概说的就是他们,余霭霞和王菲都是这类人。
“霭霞,既然决定回来了,那以后你们一家四口就好好过日子。我在霞飞路的那套别墅还空着,改天让人收拾出来,给你们住。”
这是余成安说的话,自己的女儿毕竟有过那样的事,在何家面前,该撑的场面,还是要撑。
暗示的话说到最明显,谁也不能装糊涂。
何铭威跟着附和,“我们老了,也没什么可以求的,只希望你们这些晚辈能过得好,让我们少c些心。”
搬家不过是早晚的事。
余应晚却突然开口要住校,余霭霞不过问,何致远没意见,到头来,送她的还是何景梧。
又是黄昏。
余应晚蹲在房间内收拾行李,橘色的夕阳透过窗,落她的白色连衣裙,以及姜黄色的木质的地板上,光影深浅交错,她眉目沉静,像极了那年金台寺铺了满地的银杏叶。
何景梧站在门口,拇指滑过打火机的齿轮,指尖的光影明明灭灭,他想点烟,又没点。
“站着干什么?没见我箱子关不上吗?”
余应晚没回头,她不敢看何景梧现在是什么表情,用一种非常轻松的姿态问他,“何景梧,我以后……还能使唤你做事么?”
何景梧走到她身侧,三两下的便将那些衣服塞进箱子,又匆匆扫过她带的那些东西,“这些不用带,家住的这么近,随时可以回来。”
“带着吧。”余应晚从他手里拿过布娃娃,“留在家里不安全。”
余应晚又单独拿出一个行李箱装娃娃,总共十来个,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名字,陪她从九岁到十九岁,知道她和何景梧发生的事。
何景梧不解,“不安全?”
“是啊。”余应晚抬头,冲他笑,“万一它们说漏嘴,把我们的事告诉别人了怎么办?”
从开始道现在,她所有的安静似乎等的就是这一刻。
何景梧问:“余应晚,你什么意思?”
余应晚站起身,神色平静,口气极淡,“何景梧,不要让我做我不到的事情,我学不来你们商场上那一套,我喜欢你,藏不住。”
她的声音很轻,没有半点威胁或者逼迫,就像在说不要让她吃青椒那般,请求中带着一点点撒娇,还有烦恼。
她说她喜欢他,可是,她的意思很明显,喜欢他很苦恼。
他僵了身体。
余应晚也累了,她本无意争吵,瘫坐在床上,痛恨这般干什么都不彻底的自己。
夕阳沉沉,窗外鸟鸣婉转。
她突然冒出个奇怪的想法,如果自己是余霭霞,肯定有法子不让何景梧走。
可她是余应晚,她这辈子注定学不来余霭霞,也不能g干脆脆的当何静安。
肆意放纵到极致,或乖巧隐忍到极致。ωIи10cIτγ.c噢м(win10city.com)
--
房间面积不大,东西却堆得满满的,一半是各式各样的书籍,一半是情趣玩具。
人总是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,不管用什么方式。
何景梧实在想不起来,自己跟余应晚的关系是何时发生的变化。
如同想不起来读书时的哪一天,黑板上的粉笔字突然长了毛边,再反应过来,已经戴上眼镜。
可是他清楚的记得,余应晚十八岁生日。
那天,何景梧在公司加班,很晚才回家,他以为小姑娘早就睡了,便没开灯。
洗漱完毕,何景梧躺上床,伸手触碰到一具温热的身体。
她躺在他的床上,大腿根部沾着斑驳的血迹,身体不断发抖的,脸色苍白的如纸。
何景梧有那么一瞬间,想打电话叫救护车。
再后来,他看见了床头的玩具。
她说,何景梧,你不要的东西,我也不想要了。
他的小姑娘病了。
他带她去看过很多心理医生,这间屋子里也摆着越来越多的书。
从《学记》到叶圣陶,从蒙台梭利到杜威,从弗洛伊德到荣格。
他们都是古今中外着名的教育学家,心理学家,名字印在一届又一届的教科书上,是权威的代表。
可是他们没有说,该怎么才能治好余应晚。
后来,他也病了。
何家和余家数十年没坐在一起吃饭,再聚一起,气氛是说不出的尴尬。
余应晚对何家那边的人基本没什么印象,只记得何铭威除了何致远外,还有三个孩子,两个在国外,留在洛桑定居的是他最小的女儿何静安。
何静安长得就像她的名字那般,温婉沉静,举手投足间,很是优雅。
众人有意将余应晚推到余霭霞和何致远的中间那个位置,明示暗示几次。
她站在原地,不肯动。
余成安的脸色有些不好,正要说话,只听何静安道:“行了晚晚,你坐在我这边吧。”
何静安坐在最末处,替众人布菜。
象牙筷敲击瓷碗,叮当作响,她的动作小心而又得t,让人舒心,每个人的碗里菜色都不尽相同,就连分量都不一样。
“爸,您有高血压,荤腥要少沾。”最后到了余应晚,何静安放下筷子,轻声询问她的意见,“晚晚,可有什么不爱吃的菜?”
余应晚猛得立起身子摇头,莫名有些拘谨。
何静安笑着说:“不用紧张,都是自家人。”说着,随意替她挑了几样可口蔬菜,还给她夹了一只j腿,“你太瘦,该多吃点。”
整餐饭局,沉闷而又无聊。
余成安会原谅余霭霞,是意料之中的事,毕竟,余家就这么一个孩子。
何铭威原谅余霭霞,余应晚也能理解。
余成安虽然退休,政界的威望还在,趁着最后的余热,何家如果自己又争气,路会越来越好走。
最让余应晚不明白的是,何致远竟然也能原谅余霭霞,如果真正爱过的话。
余霭霞确实是令人难忘的女子。
她生得美而娇艳,尤其是那双凤眼,狭长的眸,眼角处上扬,不笑都狐媚勾人的那种。
她的t态也很好,四肢纤细,柳腰直背,浅蓝色的碎花裙,背后的部分遮一半漏一半,隐约可见白皙水嫩的肌肤。
但跟同样温婉典雅的何静安相b,她又太不象话,吃饭中还不时的同何致远低语,两人看上去感情不错。
话题移到孩子们身上。
余霭霞终于抬头看了余应晚和何景梧一眼,淡淡微笑,算是打过招呼,过后又开始跟何致远低声聊天,仿佛坐在对面的,不是她的儿女,只是两个刚认识的人。
余霭霞可不是故意的,余应晚敢保证,她看过电视上王菲无视记者镜头,坐在谢霆锋身后玩手机的那张照片,也是这般姿态。
有些人即使身处人群,也跟人群隔着一层,不食人间烟火大概说的就是他们,余霭霞和王菲都是这类人。
“霭霞,既然决定回来了,那以后你们一家四口就好好过日子。我在霞飞路的那套别墅还空着,改天让人收拾出来,给你们住。”
这是余成安说的话,自己的女儿毕竟有过那样的事,在何家面前,该撑的场面,还是要撑。
暗示的话说到最明显,谁也不能装糊涂。
何铭威跟着附和,“我们老了,也没什么可以求的,只希望你们这些晚辈能过得好,让我们少c些心。”
搬家不过是早晚的事。
余应晚却突然开口要住校,余霭霞不过问,何致远没意见,到头来,送她的还是何景梧。
又是黄昏。
余应晚蹲在房间内收拾行李,橘色的夕阳透过窗,落她的白色连衣裙,以及姜黄色的木质的地板上,光影深浅交错,她眉目沉静,像极了那年金台寺铺了满地的银杏叶。
何景梧站在门口,拇指滑过打火机的齿轮,指尖的光影明明灭灭,他想点烟,又没点。
“站着干什么?没见我箱子关不上吗?”
余应晚没回头,她不敢看何景梧现在是什么表情,用一种非常轻松的姿态问他,“何景梧,我以后……还能使唤你做事么?”
何景梧走到她身侧,三两下的便将那些衣服塞进箱子,又匆匆扫过她带的那些东西,“这些不用带,家住的这么近,随时可以回来。”
“带着吧。”余应晚从他手里拿过布娃娃,“留在家里不安全。”
余应晚又单独拿出一个行李箱装娃娃,总共十来个,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名字,陪她从九岁到十九岁,知道她和何景梧发生的事。
何景梧不解,“不安全?”
“是啊。”余应晚抬头,冲他笑,“万一它们说漏嘴,把我们的事告诉别人了怎么办?”
从开始道现在,她所有的安静似乎等的就是这一刻。
何景梧问:“余应晚,你什么意思?”
余应晚站起身,神色平静,口气极淡,“何景梧,不要让我做我不到的事情,我学不来你们商场上那一套,我喜欢你,藏不住。”
她的声音很轻,没有半点威胁或者逼迫,就像在说不要让她吃青椒那般,请求中带着一点点撒娇,还有烦恼。
她说她喜欢他,可是,她的意思很明显,喜欢他很苦恼。
他僵了身体。
余应晚也累了,她本无意争吵,瘫坐在床上,痛恨这般干什么都不彻底的自己。
夕阳沉沉,窗外鸟鸣婉转。
她突然冒出个奇怪的想法,如果自己是余霭霞,肯定有法子不让何景梧走。
可她是余应晚,她这辈子注定学不来余霭霞,也不能g干脆脆的当何静安。
肆意放纵到极致,或乖巧隐忍到极致。ωIи10cIτγ.c噢м(win10city.com)
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