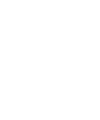十九、欢淫
浸淫床榻之欢久了,少年也从原始的蒙昧渐渐觉出乐趣来,动情了也会自发勾着他的腰。有段时间太忙没见,久别重逢他还想着和人聊聊近况,倒是崔建军支支吾吾不愿多讲,后麵干脆跑来主动讨亲。刘源使心眼逗他,蜻蜓点水表示一下,又故作君子和他聊些不咸不淡的,看着人变化莫测的表情差点没笑出声。纠结半天,建军终于放弃脸麵,跨在他大腿上磨蹭,不管不顾地搂着自己乱亲一气。刘源不再假装看书,食指毫无阻碍地插进渴望的穴肉。他居然提前扩张好了,怪不得进来的时候满脸春色。想到他屁股还在流水就大摇大摆在外麵晃,刘源没由来的妒火中烧,咬着耳朵説了点过分的荤话。建军涨红了脸,嘴里嘟嘟囔囔下麵却含着他的手指轻微收缩,他没注意到,和刘元在一起久了,身体已经慢慢开始习惯掌控以及之后的快感。首长很满意这种变化,匠人亲手採石雕刻的璞玉和展览柜的成品不是一回事,自己的作品是倾注心血和感情的。
“春天来了……”
建军听到声音,浑身打了个激灵,下意识想往里躲。嗡嗡的机械振动,他被佈帛蒙着眼睛,手脚被红绳捆紥在一起,最多隻能蹭蹭床单,连坐起来都办不到。就在副司令在外间和旅长师长轮流谈话的时候,他在这间暗无天日的房间里被压迫去了两次。房门很单薄,儘管锁上了,脚步声、来者高低不同的嗓门、首长低沉而不容置喙的命令还是从门缝里丝丝缕缕地鑽进来。幸而他嘴里还多了一个口球压着舌头,不至于让他不自觉叫出声。现在房门打开了,儘管建军知道门外不会有第二个人,视野受阻还是让他不免担忧地联想到可怕的情节。
“你看看,把床弄成这样。”这对崔建军没什么攻击力,毕竟又不是他自告奋勇要体验五花大绑的。建军像条鱼一样在床上弹动,黏糊糊的液体掛的身上到处都是。他身上系的是刘源从日本的绳艺书上学来的绳结,麻绳从两肋腋下穿行至大腿腰部,正好是无法行动又不至血液不畅的地步。他在原地欣赏了一会自己的作品,直到不满的呜呜声越来越大才走了过去。他知道他想要什么,食指伸进口球的孔洞,触到柔软的舌麵。建军仰着脑袋却看不见他,挣紥着想扯掉桎梏,刘源安抚地拍了拍他赤裸的肩膀:“安静。”
也许是刘源扯动了绳子一端,绳结缓缓地开始运动,胸前的结顶在乳头上,私处的结慢慢陷进穴口抵着阴囊,没打磨干净的粗糙纤维刮擦着皮肤,刺疼的痒意难以忽略地掠过脊椎。口水滴滴答答地顺着合不拢的嘴角流下,随着绳结收紧,还埋在身体里的按摩棒愈发卖力起来,正巧一端顶在腺体,不过一两分鐘他就难以忍受地射在床单上。刘源坐在離他稍远的地方,隻靠拉紧放缓绳子来操纵他。小崔看不见自己这副煽情的样子,他稍稍一拉就把小号手悬空提溜起来,私密部位暴露在空气里。乳头红肿着等着人捏,平坦的小腹隐隐显出硅胶软棒的形状,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把那匹红佈濡溼了,紧紧黏在眼皮上。
在解放他之前,还有一件事。首长从大衣内袋里掏出那把两用的手枪,把子弹叮叮当当地卸下来倒在桌上,建军听见响动,知道他要干什么,但当塞在身体里的死物被取掉,冰冷的金属靠在温热的皮肤上时,还是惊了一大跳。枪管在会阴处磨蹭,他反射性地想挪开,反而被绳子缚的更紧;它似乎变得像蛇一样细长、弯曲,枪口从臀缝嵌入一小块,接着是修长的枪身。这是把很漂亮的盒子枪,机械凹凸不平的设置顶着肠壁,刺激的他后脖梗都缩了起来。扳机扣动了,伴随着喀噠几声轻响,首长把枪取出,手指伸进已经被拓过一遍的肠肉。小号手还在为从里麵拍摄而羞恼,被按到熟悉的地方又鬍乱叫起他的名字,北方人的儿话音割捨不掉,“刘源儿”听起来调皮又大胆。
等他终于被仰麵推倒在床上,下体已经潮溼的一塌糊涂,未待首长顶弄几下就夹紧他的腰,催他快些。刘源从善如流地搔搔他的下巴,看他像隻猫一样扬起脖子瞇眼睛。他们换着法子在简陋的小床上做爱,有时像鱼,有时像狗,还有时像鸟。肉体在情爱里达成了某种无言的默契,哪怕不説话,从些微的动作和神态就能感知对方的快乐。建军跪在床上,上半身已经脱了力,趴在被褥上休息,刘源把着他的腰肏,屁股抬高,撞击出直白的声响。每次看见他咬着牙或者叼住床单,首长都会故意笼住他吐水的阴茎,非逼的他忘情不可。他不会説甜言蜜语,不过对刘源而言没什么,他喜欢听崔健的声音,説什么都行。迷乱的气息随着军队晚间突兀急促的号声而渐渐停息,首长替他擦掉股间的白液,整理好衣服,同他随意聊一会天。
“你之前不是説要回家看看吗?”刘源从抽屉里裁出一张假条,籤好名:“拿着,什么时候都行,想待几天就待几天,你父母该想你了,去报个平安也好。”
崔建军接过纸条和証件,连首长都催,他再不回去真有点説不过去了。打了招呼,收拾好行李,记下朋友们央他带的各式礼物,啟程前几日,唐山发生大地震,铁路全线中断,计划流产。当时沮丧的建军一定不会想到,不过小半年,他就成功地回到了北京。
“春天来了……”
建军听到声音,浑身打了个激灵,下意识想往里躲。嗡嗡的机械振动,他被佈帛蒙着眼睛,手脚被红绳捆紥在一起,最多隻能蹭蹭床单,连坐起来都办不到。就在副司令在外间和旅长师长轮流谈话的时候,他在这间暗无天日的房间里被压迫去了两次。房门很单薄,儘管锁上了,脚步声、来者高低不同的嗓门、首长低沉而不容置喙的命令还是从门缝里丝丝缕缕地鑽进来。幸而他嘴里还多了一个口球压着舌头,不至于让他不自觉叫出声。现在房门打开了,儘管建军知道门外不会有第二个人,视野受阻还是让他不免担忧地联想到可怕的情节。
“你看看,把床弄成这样。”这对崔建军没什么攻击力,毕竟又不是他自告奋勇要体验五花大绑的。建军像条鱼一样在床上弹动,黏糊糊的液体掛的身上到处都是。他身上系的是刘源从日本的绳艺书上学来的绳结,麻绳从两肋腋下穿行至大腿腰部,正好是无法行动又不至血液不畅的地步。他在原地欣赏了一会自己的作品,直到不满的呜呜声越来越大才走了过去。他知道他想要什么,食指伸进口球的孔洞,触到柔软的舌麵。建军仰着脑袋却看不见他,挣紥着想扯掉桎梏,刘源安抚地拍了拍他赤裸的肩膀:“安静。”
也许是刘源扯动了绳子一端,绳结缓缓地开始运动,胸前的结顶在乳头上,私处的结慢慢陷进穴口抵着阴囊,没打磨干净的粗糙纤维刮擦着皮肤,刺疼的痒意难以忽略地掠过脊椎。口水滴滴答答地顺着合不拢的嘴角流下,随着绳结收紧,还埋在身体里的按摩棒愈发卖力起来,正巧一端顶在腺体,不过一两分鐘他就难以忍受地射在床单上。刘源坐在離他稍远的地方,隻靠拉紧放缓绳子来操纵他。小崔看不见自己这副煽情的样子,他稍稍一拉就把小号手悬空提溜起来,私密部位暴露在空气里。乳头红肿着等着人捏,平坦的小腹隐隐显出硅胶软棒的形状,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把那匹红佈濡溼了,紧紧黏在眼皮上。
在解放他之前,还有一件事。首长从大衣内袋里掏出那把两用的手枪,把子弹叮叮当当地卸下来倒在桌上,建军听见响动,知道他要干什么,但当塞在身体里的死物被取掉,冰冷的金属靠在温热的皮肤上时,还是惊了一大跳。枪管在会阴处磨蹭,他反射性地想挪开,反而被绳子缚的更紧;它似乎变得像蛇一样细长、弯曲,枪口从臀缝嵌入一小块,接着是修长的枪身。这是把很漂亮的盒子枪,机械凹凸不平的设置顶着肠壁,刺激的他后脖梗都缩了起来。扳机扣动了,伴随着喀噠几声轻响,首长把枪取出,手指伸进已经被拓过一遍的肠肉。小号手还在为从里麵拍摄而羞恼,被按到熟悉的地方又鬍乱叫起他的名字,北方人的儿话音割捨不掉,“刘源儿”听起来调皮又大胆。
等他终于被仰麵推倒在床上,下体已经潮溼的一塌糊涂,未待首长顶弄几下就夹紧他的腰,催他快些。刘源从善如流地搔搔他的下巴,看他像隻猫一样扬起脖子瞇眼睛。他们换着法子在简陋的小床上做爱,有时像鱼,有时像狗,还有时像鸟。肉体在情爱里达成了某种无言的默契,哪怕不説话,从些微的动作和神态就能感知对方的快乐。建军跪在床上,上半身已经脱了力,趴在被褥上休息,刘源把着他的腰肏,屁股抬高,撞击出直白的声响。每次看见他咬着牙或者叼住床单,首长都会故意笼住他吐水的阴茎,非逼的他忘情不可。他不会説甜言蜜语,不过对刘源而言没什么,他喜欢听崔健的声音,説什么都行。迷乱的气息随着军队晚间突兀急促的号声而渐渐停息,首长替他擦掉股间的白液,整理好衣服,同他随意聊一会天。
“你之前不是説要回家看看吗?”刘源从抽屉里裁出一张假条,籤好名:“拿着,什么时候都行,想待几天就待几天,你父母该想你了,去报个平安也好。”
崔建军接过纸条和証件,连首长都催,他再不回去真有点説不过去了。打了招呼,收拾好行李,记下朋友们央他带的各式礼物,啟程前几日,唐山发生大地震,铁路全线中断,计划流产。当时沮丧的建军一定不会想到,不过小半年,他就成功地回到了北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