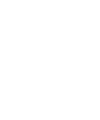二十二、北京(正文完结)
然后我最好的哥们,张领,得到一份冒名的判决。刘源对我说他安排好了一切,我只用咬死东西都是他的,录音机里的磁带不属于自己。我正是这么做的,那时我惊慌失措,只能抓住身边唯一一根救命稻草。我一个人待在隔离的房间里,除了一次探访和两次讯问,再没有人找过我。我没註意刘源通知我时反常的轻柔语气,我只顾着翻来覆去地想念父母兄弟,童年伙伴,冬日早晨安静的空军大院;我想活,想正常地走在街道上,同任何一个囚犯一样害怕流放与死亡。我向虚空许下荒诞不经的发愿,之后又嘲笑自己的幻想。新中国没有神佛,毛主席去世了,谁会回应我的许愿?记不清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,两三天,三五天,半个月,都差不多。
我被带进一间屋子,坐在侧边的位子上,迟钝地註视着依次进入的法官、穿团级军装的陪审员和刘源,以及我桌上的证人牌子。证人?门推开了,我看见走上被告席的张领。
「张领!这不是你干的,为什么你会来?」他凄凉地望了我一眼,嘴边掛着一个强挤出的笑:「老崔……」
「证人无端喧哗,藐视法庭秩序,责令离开法庭!」法槌落下,两个士兵迅速抄起我的胳膊,拖着我离开房间。我没能参与走过场的审判。
第二天我被释放了。我同游魂一样走在路上,所有人都对我避之不及。来到文工团的小楼,宿舍门大开,抽屉翻的乱七八糟,磁带和杂志全不见了。张领的被子摊开在床上,衣裳不翼而飞,撞开阳台的门,瓷砖台面上只有一个孤单的牙杯。我总觉得他没有走,只是出去踢球,晚上就会推开门朝我亲热地叫喊……我无知无觉地站起身,徘徊至一处公告栏,上面是鲜红的大字报:「文工团弦乐组张领私藏资產阶级黄色磁带、书刊,恶毒攻击詆毁毛主席,是典型反军乱军的现行反革命分子,四川革命委员会判决其劳动改造20年……」
禁闭半月的虚弱无力被这张不可挽回的判决重新点燃,冲进司令部时我的手还在不受控製地打哆嗦,刘源坐在书桌后,同我之前进来的无数次一样。我用力摔上门,不管不顾地朝他大叫:「为什么?为什么要让他替我受罪?」
「小崔……」
「不要叫我,他人现在在哪?」
「去青海的路上。」
「你让张领当替罪羊,你怎么逼他的?20年,你让他去青海劳改20年?万一他回不来呢?」
刘源收敛了温和的态度,换上他惯常的训斥口吻:「崔建军,你才是应该反思的人。他是为了救你,不是你,所有人都没这出事!你知道我为你跑了多久吗?」我正瞪着他,目光转向他眼角加深的鱼尾纹,没有言语,「呵,还有他爸,埋了多少个坑,就等着推我下去,踩上一万只脚……你不觉得羞耻吗?你现在是最安全的人,有什么资格质问我?」
难以控製的泪水涌上眼眶,我擦了擦脸,尽量保持声音清晰:「别转移话题,你骗了他!」
「他是自愿的,他愿意为你去死。」
我再也听不下去了,冲到办公桌前,抬手扫掉一个笔筒,鋥亮的钢笔、古朴的毛笔滚了一地,红木桌子拍的山响:「是你指使他的!如果没有你拍板,他怎么可能这样干?」
他没有反驳,镜片后的眼睛毫无波动:「为了救你。」
「我没有向你乞求,」望见他嘲弄的神色,我发觉自己的话不对,当时我确实惊慌失措地攀附他,但我绝不知道会是这样,「我不用朋友换自由,我愿意坐牢!我自己的祸自己承担,让我去……」
「去死?」求生对每个人都是最大的诱惑。我咽了咽口水:「对!」
「你不会这么做,我们都清楚。」
「我会,因为这是我的错!你又有什么资格分配别人的命运?就因为你是司令,呼风唤雨,你就可以随意让一个人去受半辈子苦?你觉得我会为此安心?他是我最好的兄弟!我凭什么这么对他?」我喃喃着,质问变成了自问,罪恶和背叛攥紧咽喉,挤出苦涩的汁水。张领是我在文工团认识的第一个朋友……
「我说过,只要你在我身边,你就不会有事。」
我向后退了一步,不可置信地盯着刘源。当然,除了爱,还能有什么别的理由让刘首长冒这么大的风险偷天换日?我痛苦地感到跳动的心脏还在轻颤。可我当初又为什么爱上他?绝不是草菅人命,也不是漠视他人。平等是假的,自由是假的,我享受的一切甚至生命都是靠权力换来的。我终于正视了我一直不愿面对的事实,可代价已经付出,我什么都改变不了。
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,夜晚由一滴水扩散成整片海洋。刘源不在,王秘书不在,世界失语般安静。我身上只披了件单衣,这时才觉出冷,可我现在没心思顾及。我强压住心底翻腾的风暴,在硬壳封皮的《牛虻》里找到一把钥匙。屋子里很安静,我深吸一口气,打开办公桌的抽屉。
抽屉里的东西并不多。一根竹笛,一本牛皮本,一块姓名章,还有一摞文件,我在纸堆里如愿以偿地抽出三年来的档案和证件。除了他的东西,还有几张格格不入的乐谱。带笛子的摇滚乐……我没有带走它。
在那个密不透风的深夜,我收好了一切东西。宿舍没什么多余的物品,音乐、文学、朋友,一齐烟消云散,唯一能证明它们存在的是脑海里并不可靠的回忆。我没有同任何一个人道别,用一直闲置的假条在车站买了回家的票。成都的肥沃土壤同我五年前第一次踏上时没什么两样,一路上我搂着包裹,紧张地关註周围的风吹草动,生怕有人突然冲进来把我押走。
西南的湿润与绿意自窗外抽丝般流失,故乡正在前边招手,并不能带来安心的感觉。我没有欣赏风景的气力,在座位上昏昏沉沉的做梦,直到乘务员不耐烦地将我推醒。人潮汹涌的月台上没有警察等我,这是唯一安慰的事。苍白的日光刺破云层,北境苍茫的风刮去旅客一身浊气,同行讲四川话的一家三口在拐角处消失,小男孩步履蹣跚的背影融进嘈杂声,而我独自向前走着,走着,满心空茫地走进北京。
崔健
1981年1月1日
我被带进一间屋子,坐在侧边的位子上,迟钝地註视着依次进入的法官、穿团级军装的陪审员和刘源,以及我桌上的证人牌子。证人?门推开了,我看见走上被告席的张领。
「张领!这不是你干的,为什么你会来?」他凄凉地望了我一眼,嘴边掛着一个强挤出的笑:「老崔……」
「证人无端喧哗,藐视法庭秩序,责令离开法庭!」法槌落下,两个士兵迅速抄起我的胳膊,拖着我离开房间。我没能参与走过场的审判。
第二天我被释放了。我同游魂一样走在路上,所有人都对我避之不及。来到文工团的小楼,宿舍门大开,抽屉翻的乱七八糟,磁带和杂志全不见了。张领的被子摊开在床上,衣裳不翼而飞,撞开阳台的门,瓷砖台面上只有一个孤单的牙杯。我总觉得他没有走,只是出去踢球,晚上就会推开门朝我亲热地叫喊……我无知无觉地站起身,徘徊至一处公告栏,上面是鲜红的大字报:「文工团弦乐组张领私藏资產阶级黄色磁带、书刊,恶毒攻击詆毁毛主席,是典型反军乱军的现行反革命分子,四川革命委员会判决其劳动改造20年……」
禁闭半月的虚弱无力被这张不可挽回的判决重新点燃,冲进司令部时我的手还在不受控製地打哆嗦,刘源坐在书桌后,同我之前进来的无数次一样。我用力摔上门,不管不顾地朝他大叫:「为什么?为什么要让他替我受罪?」
「小崔……」
「不要叫我,他人现在在哪?」
「去青海的路上。」
「你让张领当替罪羊,你怎么逼他的?20年,你让他去青海劳改20年?万一他回不来呢?」
刘源收敛了温和的态度,换上他惯常的训斥口吻:「崔建军,你才是应该反思的人。他是为了救你,不是你,所有人都没这出事!你知道我为你跑了多久吗?」我正瞪着他,目光转向他眼角加深的鱼尾纹,没有言语,「呵,还有他爸,埋了多少个坑,就等着推我下去,踩上一万只脚……你不觉得羞耻吗?你现在是最安全的人,有什么资格质问我?」
难以控製的泪水涌上眼眶,我擦了擦脸,尽量保持声音清晰:「别转移话题,你骗了他!」
「他是自愿的,他愿意为你去死。」
我再也听不下去了,冲到办公桌前,抬手扫掉一个笔筒,鋥亮的钢笔、古朴的毛笔滚了一地,红木桌子拍的山响:「是你指使他的!如果没有你拍板,他怎么可能这样干?」
他没有反驳,镜片后的眼睛毫无波动:「为了救你。」
「我没有向你乞求,」望见他嘲弄的神色,我发觉自己的话不对,当时我确实惊慌失措地攀附他,但我绝不知道会是这样,「我不用朋友换自由,我愿意坐牢!我自己的祸自己承担,让我去……」
「去死?」求生对每个人都是最大的诱惑。我咽了咽口水:「对!」
「你不会这么做,我们都清楚。」
「我会,因为这是我的错!你又有什么资格分配别人的命运?就因为你是司令,呼风唤雨,你就可以随意让一个人去受半辈子苦?你觉得我会为此安心?他是我最好的兄弟!我凭什么这么对他?」我喃喃着,质问变成了自问,罪恶和背叛攥紧咽喉,挤出苦涩的汁水。张领是我在文工团认识的第一个朋友……
「我说过,只要你在我身边,你就不会有事。」
我向后退了一步,不可置信地盯着刘源。当然,除了爱,还能有什么别的理由让刘首长冒这么大的风险偷天换日?我痛苦地感到跳动的心脏还在轻颤。可我当初又为什么爱上他?绝不是草菅人命,也不是漠视他人。平等是假的,自由是假的,我享受的一切甚至生命都是靠权力换来的。我终于正视了我一直不愿面对的事实,可代价已经付出,我什么都改变不了。
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,夜晚由一滴水扩散成整片海洋。刘源不在,王秘书不在,世界失语般安静。我身上只披了件单衣,这时才觉出冷,可我现在没心思顾及。我强压住心底翻腾的风暴,在硬壳封皮的《牛虻》里找到一把钥匙。屋子里很安静,我深吸一口气,打开办公桌的抽屉。
抽屉里的东西并不多。一根竹笛,一本牛皮本,一块姓名章,还有一摞文件,我在纸堆里如愿以偿地抽出三年来的档案和证件。除了他的东西,还有几张格格不入的乐谱。带笛子的摇滚乐……我没有带走它。
在那个密不透风的深夜,我收好了一切东西。宿舍没什么多余的物品,音乐、文学、朋友,一齐烟消云散,唯一能证明它们存在的是脑海里并不可靠的回忆。我没有同任何一个人道别,用一直闲置的假条在车站买了回家的票。成都的肥沃土壤同我五年前第一次踏上时没什么两样,一路上我搂着包裹,紧张地关註周围的风吹草动,生怕有人突然冲进来把我押走。
西南的湿润与绿意自窗外抽丝般流失,故乡正在前边招手,并不能带来安心的感觉。我没有欣赏风景的气力,在座位上昏昏沉沉的做梦,直到乘务员不耐烦地将我推醒。人潮汹涌的月台上没有警察等我,这是唯一安慰的事。苍白的日光刺破云层,北境苍茫的风刮去旅客一身浊气,同行讲四川话的一家三口在拐角处消失,小男孩步履蹣跚的背影融进嘈杂声,而我独自向前走着,走着,满心空茫地走进北京。
崔健
1981年1月1日